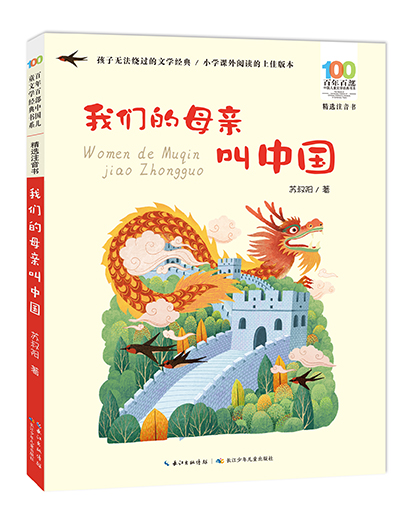- 作者简介
- 编辑推荐
他曾经两次横穿中国,从南北两线走进帕米尔高原。
他曾经三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他曾经四次探险怒江大峡谷。
他曾经六上青藏高原。
他多年跋涉在横断山脉。
他曾经两赴西沙群岛探险。
他在大自然中凿空探险40年。
他的代表作有四部描写在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和几十部大自然探险奇遇故事。
他的作品曾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2010年安徽省人民政府为他建立“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工作室”。
他2010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
他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被列为林格伦文学奖候选人。
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
内容推荐
作者用优美的文笔,生动展现了我国科学家为保护海洋顶级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热情讴歌了他们长年累月冒着生命危险在海底的追梦之旅。作品同时附有大量精彩照片,向读者展示了难得一见的如梦如幻的海洋生物世界,自然之美赏心悦目。
作品将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力求唤起大众的海洋意识,树立生态道德观念,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道理。
目录
引子
发现钻石红珊瑚?
吃出了珍珠
珊瑚梦
流星雨
珊瑚狂舞
谁在偷袭?
月亮鱼 太阳鱼
三只螃蟹分类
飞箭齐射
南沙群岛有潟湖
剑鱼疯狂
寻找黑宝石
美人鱼
炮弹鱼发起攻击
“魔鬼”很淘气
天上掉下个小蝠鲼
海上漂起红带子
小笪的故事
还是那个鹿回头?
遭遇轰炸
警报:海底躺着核弹
名片掉色
梦想的光辉
深海更迷人
刘先平40年大自然考察、探险主要经历
阅读部分章节
现钻石红珊瑚?
世界上只有一种呼吸,吐纳之间具有惊天动地的神奇。这就是大海的呼吸,它以潮起潮落宣示着生命律动的波澜壮阔。
大海的灵魂是月亮。月亮虽远在38.4万千米外的高空,却赋予了大海血脉的张弛、生物的荣衰。难道月亮是从大海出走,却又时时眷顾故乡的游子?难道这也是引力波的作用?
我和李老师在西沙群岛读海。
椰树的羽叶在微风中絮语,永兴岛和七连屿之间的红海门海况很好。午后的一场小雨将蔚蓝的天空洗得透明、晶莹。靛青的大海闪着红晕。只有在南海极目天空和大海,你才能领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春来江水绿如蓝”所说的那种色彩相融与变幻的美妙。
细浪悠闲地漫步。远处时而蹿起巨大的水花,如大漠孤烟——是鲸,是鱼?
读得我思绪如大海一样翻涌……
不知为什么,山海关那幅千古传颂的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
李老师在退潮后的礁盘上拾着贝壳,以另一种方式读海,探视大海深处的五彩缤纷。
昨天,她在一个小水凼中,看到一条灰黑的虾虎鱼正驮着一只彩色的枪虾寻找猎物。那位穿着花里胡哨的“彩衣骑士”在虾虎鱼的导猎下张牙舞爪,显得神气活现。看久了,才发现枪虾竟然是个近视眼,需要借助虾虎鱼敏锐的眼力才能捕猎成功。李老师故作扰动,可还未看清仓皇的枪虾是怎么动作的,虾虎鱼就以闪电般的速度驮着“骑士”,钻进了一个已掘出的洞里……它们组成的生命共同体,令她赞叹不已。
“你看,那边是什么?就在露出来的珊瑚礁上面!”李老师惊乍乍地喊出声,还未等我答话——其实我什么也没看到,在野外,她一向眼尖,常常比我先发现新奇——她已经一溜儿小跑过去了。
“哎,正涨潮哩。当心!”我说。
潮水已摧起水波向这边涌来。她不是不知道。别看落潮后露出的礁盘看似平坦,但坑坑洼洼,小水凼密布;更有软礁盘,就像沼泽地,一脚下去,就是个大窟洞。是什么宝贝使她如此着急?慌得我连忙追去。
李老师涉水声很大,溅起的水花乱飞。潮水来得真快,我心里更急,只得拼命追去。
只见李老师从礁石上抓了个物件,转身飞快地抄近路向岸边跑。
我们的裤子、鞋子都湿了。我直埋怨她:“你没看到涨潮吗?”
“没看到我会那样急着跑?现在你还能再看到那块礁石?”
真的,它已被潮水淹得只露出个尖尖。
“什么宝贝?”我问。
她把右手一摊,一块深红色的珊瑚躺在手心。说是块状,却长不长、圆不圆的,然而那艳红的色彩却很热烈。
“是红珊瑚?”她问。
我心里一激灵,但并不敢肯定。在西沙群岛的几十天里,很多渔民都说过红珊瑚的神奇、宝贵。其实,人类早已认识到珊瑚的价值,不仅将它列为四大有机宝石之首,还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而红珊瑚更是珊瑚中的极品,可我们至今还未在大海中见过,渔民们也没见过。这更引起了我们的无限向往。
我把那块深红的珊瑚审视了一番,发现它像海绵,身上有很多小孔洞,一摇,却很坚硬,没有海绵的弹性。
“不太可能是红珊瑚!听说它生长在深海,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出现?”我说。
“不会是潮水打上来的吧?”李老师还沉浸在发现的快乐中。
“你是想疯了吧!红珊瑚已经是极端濒危的物种,它生长缓慢,素有‘千年珊瑚万年红’之说,价格比黄金还高。我看过一个资料,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红珊瑚于1980年采自台湾地区东北部宜兰龟山岛附近海底。这株桃红色的‘珊瑚王’,高125厘米,重75千克,分有多枝,现被台北市一家珊瑚公司收藏。有人出价500万美元,藏家还没卖哩!专家估计,它的年龄应该在2万年左右,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生长,才长到这个份上,是名副其实的大寿星。因而有人将红珊瑚称为‘海底钻石’。如果这里发现了风浪打上来的红珊瑚,谁还会披波斩浪去打鱼?每天来赶海的人不把礁盘都踩塌了?还等你这位草根探险家来捡?”我说了这么多,可一点也没减去她半分兴致。
“那你说它是不是珊瑚?”李老师说。
“看样子是。”我说。
“你能说它没有艳艳的红色,南海的热烈?”李老师说。
我语塞。
转而一想,我的确只在西沙的珊瑚岛看过生长在海底的珊瑚。我不是专家,其实并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所以管它是不是红珊瑚哩,几十年的大自然探险经历告诉我,发现就是快乐!大自然蕴藏着无穷的神奇和奥秘,怀着崇敬和朝圣的心情走万里路,一定会有发现!否则为什么我们经历过那么多艰难险阻,到了七十多岁,还像老顽童一般跑到西沙群岛来探险?科学家不是说人类对大海的认识只有1%吗?我们怎么知道它就一定不是红珊瑚哩?怎么知道它就一定不是新物种呢?李老师冒险捡来的红色珊瑚让她这么快乐,这还不值得?于是,我说:“真的,说不定它就是红珊瑚!咱们赶紧回去换掉湿衣服,晚上还有好事等着我们呢!”
我们踏着月色走向渔村,林间宁静、温馨,微风拂来椰花沁心的芬芳,淡淡的羊角花在脸上轻轻地抚摸着。椰林中,家家门口灯火辉煌。这时,身后响起一串脚步声,我回头一看,乐了:“陈司令,这么着急是往哪儿赶?”陈司令是永兴岛的驻军司令。
他笑了,示了示手里提的酒:“怎么,有好事就忘了我?”
李老师说:“哪敢!只是没想到阿山今晚办得如此隆重。这家伙做事总要制造一大串悬念,让你不能不按他说的办。”
阿山是我们第一次到西沙时在船上结识的渔民。他年轻,爱在大海中闯荡,精明,幽默。李老师常说他是渔民精英。我们一见如故,后来就是他带我们去钓石斑鱼、马鲛鱼、蓝金枪,遭遇了种种惊险,收获了无限喜悦。
“有悬念才有故事。刘老师不就是天涯海角找故事嘛!”陈司令说。
几十天的相处,我们和陈司令已是老朋友了。说着话儿,已看到阿山家门口坐了几位年轻客人。看样子,我们还是来迟了。
阿山和他的妻子阿慧怡然自得地坐在桌边喝着茶,嗑着瓜子,那几位客人则边饮茶,边吃生菜。那是一大篾盆翠嫩翠嫩、沾着晶莹水珠的生菜,显然是从阿山家菜园摘来的。既无盐,又没酱,他们却津津有味地细嚼慢咽,很绅士,可拿菜的速度并不慢。山东人就爱这样吃大葱。难道他们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但从衣着上看,应该都是广东流行的款式和色彩,特别是那位女同胞的衣着,洋溢着热带的浓烈。
李老师碰了碰我的手臂,我懂她的意思——他们这样吃生菜,就像品尝美味的水果。再看那位女同胞的脸上,明显有渴望被满足的表情——是心灵对绿色的渴望,还是绿色抚慰了心灵?
“中建岛……”她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激得我记忆闸门霎时打开。西沙群岛几乎全是珊瑚岛,岛上没有土,只有白色的珊瑚沙。多年前,守岛战士的生活条件很差,特别是蔬菜和淡水奇缺。最偏远的中建岛竟然见不到一棵树、一棵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大戈壁。有位服役两年的战士下岛探亲,当他在永兴岛上看到一棵抗风桐时,竟哭得惊天动地。过路的战友问他这是怎么了,他竟两手来回抚着婆娑的绿叶,又凑上去深情地嗅着,沉醉在绿叶的芬芳中,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对,他们就是这种神态!
难道他们也经历了长期的海上漂流?是旅行者,还是闯海者?
“你就这么请客?是不是只请大家吃海风椰韵?”李老师揶揄。
“阿姨,这就冤枉我了。不是在等你吗?马上就上菜。你可别不舍得吃啊!”说着,阿山就从屋里搬来一大盆海鲜,那盆子沉得他弯腰撅屁股。他咧着大嘴,将它往桌上一放,桌面一颤。阿山顺势装模作样地大口喘着气。
“牡蛎,好大好肥!”李老师又惊又喜,伸手一捏,冰凉,“还不赶快拿去煮!”
“当心!”我说。
“它还咬人?难道像芋螺一样有毒舌?”李老师感到诧异。
“不是,是它棱角很锋利,比刀子还快。你忘了我1983年在红树林采它,手被割得鲜血直冒?”我说。
这些牡蛎比巴掌还大,乍一看,灰头土脑的,要不是壳上染有海藻的绿色,还真能叫人以为是个石灰砣砣哩!
阿惠已将作料放到大家面前。
李老师意犹未尽:“在哪里采的?也不带我们去,吃偏食的家伙!”
阿山说:“无功不受禄。阿姨跟我下海这么多趟,还不知道我只是个钓手?螺呀,贝呀,不是撞了手,我是不会拾的。生蚝是皇甫老师带来的。”他眼色指向那位女同胞。
南海渔民称牡蛎为生蚝。西沙渔民多是从海南的谭门、文昌来的,海猎行当分得很专业——钓鱼的不捡海参、螺、贝,捡海的不钓鱼,用网的专攻布网。
先坐在那里的皇甫老师眉清目秀,脸庞白皙透红,娴淑地、静静地喝着茶。我以为她是阿山家今天从海南来的亲戚,谁知是位年轻的老师。
我不禁多看了她两眼。
看阿山还是未动,李老师有点急了:“阿山,你锅不动,瓢不响的,只搬来这么大一盆牡蛎,是只给看,不给吃的?”
我感到阿山在导演着什么,于是连连对她使眼色,可她喜欢跟他斗嘴,只顾不依不饶。
阿山在一旁站着,不吱声。一脸的无辜,无辜中藏着诡秘。
那位皇甫老师和她的同伴饶有兴致地微微笑着,等着看热闹。倒是陈司令厚道:“刘老师一定知道牡蛎是法国大餐中的美食,是法国人的最爱。巴尔扎克、雨果笔下的贵族们,不仅把生吃牡蛎当成时尚,还视牡蛎为财富、身份的标志。这是今晚的顶级美味。”
“生吃?”这下轮到李老师傻眼了!
她朝我瞄了一眼,我说:“没错。据说有的食客一餐能吃一打哩!”说实话,我虽然喜爱牡蛎的美味,在厦门、福州见到牡蛎煎饼,总要吃得心满意足才罢休,可从未吃过生的牡蛎。
和皇甫同来的身材魁梧的小袁,已打开了陈司令带来的葡萄酒,给每人斟上。
陈司令说:“难得今天大家聚在一起,缘分呀!缘分就是天下最精彩的故事。来,干了这杯,开吃!”说着,就用工具撬开了牡蛎的硬壳,白白嫩嫩的肉如水泡蛋般躺在壳里。他将各种调料放进去,用勺子一兜,就送到了嘴里,美得眉毛像跳舞一般……陡然连打了两个喷嚏……那是芥末通窍开塞的功效。
大家都开吃了,我也如法炮制。其实,我对吃生鱼片、生虾并不陌生。我生在巢湖边,每当夏日湖水淹没柳林,我就和小伙伴们边游水,边在柳树红红的须根中摸虾。巢湖的白米虾是特产,又肥又晶亮。捉到后,立即剥壳吃虾仁,满嘴溢着荷香和狂野的风浪酿就的甘醇……
“李老师,你怎么不动手?南海野生的蚝绝对没污染,营养丰富,大滋大补。”陈司令说着,顺手拿了一个放到她面前。
可李老师只是在打量这个灰疙瘩。我知道,她对生鱼片天生畏惧,更别说生吃牡蛎了。
阿山出场了:“阿姨,您当了几十年的班主任,肯定讲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学生们都动手了,您也不能光说不练啊!”说着,就拿那小工具去撬壳。
“你的激将法没用。我只是在找壳缝。我在热带雨林吃过竹虫,烤得金黄,到嘴满口奶香。你吃过?馋死你!想难为我,没门。看谁笑到最后!”李老师说。
她真的麻利地打开了壳。陈司令忙帮她加调料,可那雪白的肉体竟然蠕动起来,惊得她往后一仰——可能是它受到了调料的刺激。大家一愣。嗨,她却一勺子送到了嘴里。
“怎么还有种蟹黄的香酥感……”李老师说。
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
掌声未落,我突然忍不住叫了一声:“哎哟!”